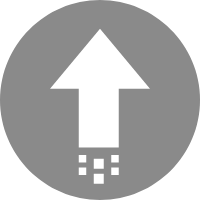说来有趣,我拥有的最早的记忆是和死亡相关的。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远古的记忆有两段。头一段是母亲拉着我的手从一辆车上下来,急匆匆地走进一个大堂里,背景里拉出电影里常有的蓝白色的长条形亮光。很奇怪的是,我对于这段记忆所拥有的居然是第三视角。大概是后来看太多电影电视剧,于是对这段记忆进行了艺术性修正了。
第二段记忆则转换回了第一视角。母亲拉着我挤进人堆里,这些人是谁我并没有留意,我的注意力都留在了这堆人围着的地方。那是一张医院的床,上面躺着一位老爷爷,盖着雪白色的被子,闭着双目,戴着呼吸面罩,插着各种样式的管,一动不动。我并不认识这位老爷爷,或者说我当时的记忆里并不知道他是谁。这时母亲拉了拉我的手,示意我打个招呼。年幼的我就顺从地向床上的老爷爷摇了摇手,但依然满脑子好奇他是谁。
稍微长大了一点,开始懂得理清亲戚关系之后,我才意识到,留在我记忆最开始的那位老爷爷应该是我的外公,那个场景应该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而这个名叫「死亡」的人生阶段,则刻在了我记忆的最开端。
我的家族比较开明,对死亡这件事并没有太多忌讳。类似于「生死有命」这样的观念伴随着我成长,以至于我一直都比较随缘佛系。有意思的是,我的家族并不信佛。逢年过节祭祀的礼仪似乎也没有特别讲究,没有什么铺张浪费,贡品也不过是苹果糖果之类的,似乎更在意的是心诚则灵。祭拜的对象也都是祖先,而不是各路神明。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存在,我们似乎更相信那些曾经陪伴过的人,即使他们已经经历了「死亡」。
我也不忌讳和恐惧死亡,我对死亡最多的情绪是可惜。还没领略够大千世界就匆匆离开,于我而言是莫大的可惜。
小时候的某一年,我准备在暑假去走川藏线,并兴冲冲地将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的同学。同学却担忧地回应道:「那不是很危险么?又是路况复杂又是高原反应的,你不怕死么?」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表达「死了又怎样?我已经看到巍峨的雪山了!」这样的逻辑。当然,后来我顺利了结束了旅行,甚至连高原反应都没遇上。但在垭口呼啸而过的高寒山风,至今仍时常在我耳边刮起。
也许是有些年纪了,近年来陆续有相熟相识或者只是认识的人离世。有的猝不及防,一觉睡去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有的与病魔斗争已久,最终还是只能面对永生的死神。我总会不自觉地代入并且衡量一下,去世的人到底活够了没有。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们是否会觉得惋惜,是否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每当这时我会发现,我体验的不是他们的死亡,而是他们的生活。
我喜欢看科幻小说,我喜欢仰望星辰大海。从宇宙的尺度下看,一个人类个体连尘埃都算不上,生或死的意义被稀释得几乎不存在,虚无主义扑面而来。但反过来想,既然生死都不重要,那第一顺位不就应该落到了令自己感受生死上么?与其贪生怕死,追逐虚无的苟活,逃离虚无的终末,不如在这一刻令自己动容,大哭,或大笑。
有酒今朝醉,可以是浓烈的威士忌,可以是绵长的干邑,可以是辛醇的朗姆,当然也可以是甜脆的菠萝啤。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