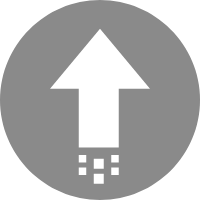第一节
胤匡武帝圣王十一年。
月牙客栈大门上的牦牛角被挂上了大红灯笼,客栈内热闹非凡,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远处,夕阳慢慢爬下巍峨的勾弋山脉,但残辉依然烧红着天,几片晚霞如烙铁般通红,砸出漫天星光。
客人们在灯笼下进进出出,已来的客人拱手迎进更多的客人,越到晚饭的时候,来的人就越多。他们三五成群,围坐在饭桌上,猜着拳,斗着酒。伙计的招呼声此起彼伏,他们肩上搭着汗巾,手举着托盘利索地穿梭于饭桌之间。饭桌上觥筹交错,各种美食或热气腾腾或冰寒覆霜,最热烈的依然是食客们的热情。
客栈里还搭了个戏台。台上的说戏人在讲着老掉牙的烂笑话,台下却还有人笑得不亦说乎。因为有了笑声,客栈内更加热闹了。
在离柜台最近的一张小桌上,却有一人静静地独食一桌。那人一身游侠打扮,衣衫风仆,双目却没有艰旅后的疲倦。一把剑倚在桌边,剑鞘上没有花俏的花纹,却是古朴地嵌着一大块沉木。他微微抬起头,望向热闹的人群,问道:「这都多少年前的古老笑话了?你的客人都是老不死吗?这都笑得出来?」
柜台上的人从算盘中抬起头,嘴角带起一丝笑意:「所以说你不懂经商之道。那些哈哈大笑的人都是我请来的托,用来调节客栈的气氛。吃饭的气氛好了,人自然就会多吃点多喝点。他们的笑不是因为笑话,而是为了钱。」
游侠半晌没吭声,良久才问:「我记得以前是没有这个戏台的,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今天是起飞日,而且是今年月力最强的展翅日。对于羽族来说,今天相当于你们人类的除夕。」
「说起起飞日,你的翅膀……」
「早就习惯了,」丁掌柜苦笑道,「生来就是个谬种,也没什么好忌讳的。今天是个好日子,苏安玄,你初来宁州,今晚就出去走走,见识一下宁州的风土人情吧!」
「嗯,等我吃完这盘鱼再说,真的很好吃……」
丁掌柜探出头来,瞧看那盘鱼:「哦,天拓海鲈呀!这是天拓海峡深沟处里抓的鲈鱼,因为太深,连鱼线都够不着,只能人潜下去抓。鲈鱼一抓上来马上用冰蝉一路冰鲜着从瀚州运过来,待冰融化立即上桌,再配上醉青阳酒,使口感更脆嫩冰爽。」
苏安玄夹起一块鱼肉,眯着眼看那像瀑布一样涌下的寒气,问道:「冰蝉?那是什么?一种调味冰?」
「不是,这是殇州大雪山里的一种蝉。这种蝉死后若捏碎其身体就会放出刺骨的寒气,我们常用来运需要保鲜的食物。」
「听起来挺不错,想不到你还有殇州的交易。还有剩余的冰蝉吗?我想要点看看。」
「拓展市场规模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喏,这里还有一瓶,送给你,不要乱用。这里的冰蝉足够将整间客栈给冰上。」羽人将青瓷瓶抛给苏安玄,后者稳稳地接住,咽下最后一口鱼肉,便站起身来。柜台上的羽人突然压低声音说:「当心你的扳指,不要露出来给人看见。更不要被辰月的人发现。铁甲依然在。」
「铁甲依然在!」苏安玄应了声,提起倚在桌边的剑,转身走出月牙客栈。
夜空被噬去了最后一片晚霞,天际泛起微弱的星光,相比之下,那轮圆月更显得明亮。月下,小镇每家每户都挂起灯笼,从远处看,就像一片通红的火海。
街巷两旁都摆起了摊位旁都竖着一根竿子,或掛招牌或飘旗子,但更重要的是都挂着一个灯笼。放眼望去,无骨灯、珠子灯、罗帛灯、八角宫灯、大红纱灯、双鱼花蓝灯、葫芦双串纱灯、藏玉镶翠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传说,以前这些花灯是为了给战胜归来的雪鹤团指路的。
大街原本不算宽阔,加上两边商位中间的人群,十分拥挤。苏安玄也挤在这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人龙中,好几次都差点掉了鞋子。
「这怎么能与天启的除夕相比,这里的人口密度是天启的好几倍呢!」苏安玄口中嘟哝着,抬眼望向星空。暗淡的星光之下,月亮格外圆亮。
人群又向前拥动,像前进的水波,苏安玄不得不将眼睛从夜空移开,随人流前进。
一低头,隔着重重人海,他看见的却只有一双眼,一双普通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眼睛。
时间像是静止了,灯笼中的火苗凝固在夜空中,整个世界仿佛都停滞,周围的喧闹像隔了一层膜,渐渐弱小下去。街道上,乃至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久久地对视着,边挂在竿上的红灯笼都为之失色。
在她眼底,苏安玄仿佛能看到一种难以言状的颜色。
四目相对,没有激烈的烟火,也没有江南烟雨的深情。一切都只是平淡,却淡得不俗,想一壶久泡的清茶,荡漾出一阵朴实淡然的清香。
就像隔着薄雾看世界,一滴浓墨滴入清水化开,亦幻亦真,恍惚间一跃千里,似已过了数百万年。顽石龟裂,水凝结冰,沧海桑田间,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它来源于世界之魂,却存在于每个人身边。此刻,它便在那两道目光的交接点处,轻轻地拨动了命运之轮。殊不知,命运的结局,却在冥冥之中被注定。
「看那!他们飞来了!」一声惊呼将苏安玄拉回世俗,人潮喧闹起来了,每个人都抬头望向天空。
只有两人在人海中张望,却始终找不到对方。苏安玄若有所失地退出人潮,闪进一条无人的小巷,靠在巷角。
比起街道上的喧闹,这里宁静许多。
这时,苏安玄才抬起头来望向天空,深蓝色的天空中布满黑点,一如北归的大雁,井然地在空中飞翔。
那便是一群新的羽人。在这个起飞日的夜晚,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这些孩子们刚过完自己的成人礼,就来到山崖上,借着当年最强的月力,第一次凝出双翼。当晶莹的双翼在他们背后凝结展开时,这才意味着他们成为真正的羽人,而那些无论如何努力,背上依然空荡荡的羽人,只能沦为无翼民。
在残酷的生存法则之下,只有强者才能以绝对的高度俯视众生。
而如今,那些新星们在天上翱翔,注定的弱者们只能站在山崖上面对巨大的圆月以泪洗面。命运总喜欢捉弄人,但其实它早被安排好,一环扣一环,没有偶然。
苏安玄靠着巷壁,望着空中划过的点点黑影,他们时而翻转,时而攀升,生涩地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快速掠过的身影令人眼花缭乱。
不经意间,苏安玄却看见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有两个羽人飞离出来,速度很快,不像是新手。而飞行的方向却是朝着苏安玄这边来的。
第二节
烛影摇曳。
面具人坐在长桌的一端,仪态端庄高雅。右手执一把精致的青铜匕首,细致地修理着修长十指上的指甲。烛光映照在他银色的面具上,泻出一丝冷酷。他身着黑衣,衣上若隐若现的斑纹,显示他的地位的高贵。
在长桌的另一头,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那一头,借着烛光,可以看到一个衣冠不整的人,黑色长袍从中间打开,露出结实的胸膛。面对满桌的菜肴,他非但没有动箸,反而举酒尽饮。桌上七歪八倒地放着各色酒壶,溢出的酒水流了一地。
酒鬼单脚支上椅子,眯着双眼看手中摇晃着的酒壶:「好久没这么畅饮过了。你没到过天启,没感受过那种形势。假若今晚喝了超过三壶酒,只要走出这个门,第二天就会有流浪狗来舔喝那还散着酒味的鲜血。」
「天启城现在就是个大棋盘,每步下子都会险象环生,那群天罗实力不可忽视。天启那边不好受啊。虽说有几个缇卫镇着,但还是老样子。三年前出现了个白发鬼,几个缇卫都无计可施。」
「在那边睡个觉都不安稳,更别说喝酒了。现在终于逃出那个该死的鬼地方了。如今有些年轻人拥着争着到天启勤王建功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凶险。根本不知道公府后门的巷道上的青砖上染了多少鲜血!」酒鬼摇着脑袋,他的胸膛连着颈项已经涨得通红,「有人说见过白发鬼,不过是个孩子,那几个缇卫连个小破孩也解决不了,顶个屁用!」
面具人陡然停下手中的匕首,冷眼望着对桌的人:「你喝醉了。」
「没有 ,没有。」酒鬼继续摇晃着脑袋,「这次跟着出来的,还有教长亲自吩咐过的一个人,女的,姓古。」
「姓古?是那个男人的亲戚?」
「不知道,教长只吩咐这个女的很重要,便宜行事。」
「看来她被神安排好了命运。来到宁州,她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只是不知道神为她安排了怎样的结局。」
酒鬼猛灌一中:「不管怎样,她和我们一样逃出了那个该死的棋局,总该值得庆幸。有多少人深陷那个棋局,想出来都不行,更何况她一女的。」
「别以为你真的走出了棋局。这整个天下何尝不是两神竞争的战场。天启城不过是当下最激烈的一角。在宁州,对于我们辰月也不轻松。由于那个男人的原因,羽族的皇族对我们辰月恨之入骨。站在别人的土地上,却又不受人欢迎,我们的一举一动自然很受限制。」面具人吹了指甲上的碎屑,抬眼望向酒鬼,嘴角似乎闪过一丝冷气。「教长有道密令,随着你来到了宁州。我刚看过了。逃出天启这角棋局的,并不只有你一人,还有一枚棋子逃了出来,但不是我们辰月的人,是名天驱。如今,他就在宁州。密令上说他带有扭转局势的火种。我们要保证火种不燃,最好是将其永远地熄灭。教长将这次行动称为‘灭火行动’。」
「一个天驱而已,为什么要我们出手?找几个『刀耕计划』的种子来就足够了。」
「这也许是那个女的来到这里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几个种子可以解决的人,是不会逃出天启这个天罗地网的。」面具人起身走到窗前。
皓月当空,远处的城镇灯火繁耀,热闹非凡,隐隐可以听到从那边传来的欢呼声。可是在两人所在的小楼周围,却十分静谧,虫鸣蛙声忽而响起。面具人抬起头来面对安静的圆月。那圆月像是一汪圆形湖泊,不起一丝波放,宁静而深不见底。千百年来,它就一直高高地俯视众生,平静地观看着一出出喜剧闹剧。
「宁州,也将要热闹起来了。」面具人静静地说。
同样的皓月之下,月光透过晶莹的羽翼照射在羽人特有的修长身躯上。两个羽人急速地飞向一栋楼房,在屋檐处稳稳地停住,然后双脚勾住横梁,将身子慢慢放下去,倒挂在屋檐上,其中一个羽人拿出小刀,撬进窗逢里,轻轻挑开锁芯。于是,两个羽人推窗而入。
然而这一切,全被躲在对面楼上的苏安玄看得一清二楚。苏安玄攀上楼檐,退后一步,纵身一跃,轻轻伏上那栋楼顶。他学着羽人倒挂在屋檐,透过窗纸偷偷张望屋内的情形。
屋内陈设像是一间雅间,书架上除了书籍,还有一两件河洛精制的瓷器。在房子的四角从天花板上垂下四盆幽兰。当中则摆放着一张古檀木做的桌子。上面是完整的一套茶具。奇怪的是,桌前并没有摆放椅子,而是放上了四盆花。
四盆花各自都只开了一朵花。
其花茎淡棕偏绿,隐约可以看到有小刺。叶则是墨绿色,呈宽卵形,叶缘有锯齿。花顶在茎顶,已经绽开,花瓣一层包着一层,如浪花向内聚拢。这是四朵月季,却比普通的月季要红艳。借着水银般的月光,鲜红的月季宛若滴血,四点腥红惊心动魄。
而那两个羽人好像就是冲着四朵月季而来的。只见他们从紧身衣内贴身抽出软绳,各自将两盆月季捆在一起。
尽管不知道两个羽人为何要偷窃月季花,但是偷窃总是错误的。正当苏安玄想现身制止时,屋内的楼梯响起了脚步声。羽人一愣,随之相互打了手势,退到屋内阴暗角落。
房门打开,一个侍者打扮的老人走了进来,双眼向房内一射,像是发现了什么,立即驻足吼道:「什么人?出来!」听其声,中气十足。语音未落,两个羽人暴起,软绳直击老人。老人似乎没有意料到有两个敌人,矮身躲开一条软绳,却被另一条软绳拽倒在地。
两个羽人似乎无心恋战,挥绳圈起月季就向窗口冲去。将近来到窗口处时,只见窗外射进一条人影,从两个羽人中间穿过。其中一个羽人被撞得向一旁跌去,另一个却发现手中的月季花被人抢走了。回头一看,只见一人手抱刚抢来的月季站在那,正是苏安玄。
第三节
羽人望了望鲜红的月季花,犹豫了一阵,拉起坐在地上的同伴,丢下月季花,继续朝窗户跑去。苏安玄见他们要逃跑也不顾手中还抱着月季,立马追上前去。在羽人跃窗前的一瞬,撬窗的那个羽人突然转身,一把小刀闪电般扎来。小刀沿着一个诡异的路径,贯穿一朵月季花,带着血红的花汁朝苏安玄射来。
因为房内空间狭小,苏安玄无处躲避,只好松开右手,奋力抓住飞来的小刀。刀是抓住了,但同时也在右手虎口留下了一条淡淡的血痕,妖红的花汁爬上了手掌。
苏安玄反手将小刀掷向羽人。这时,羽人也已经跃出窗口,背后的羽翼重新凝结出来。小刀却准确无误地贯穿一个羽人的右翼。晶莹的翼瞬间破碎,像撞碎的水晶片。水晶片散入夜空中,逐渐沙化,像细沙被风儿吹散一样,消失在明亮的圆月之下。
失去右翼的羽人失去平衡,幸亏一旁的羽人将他一把抓住。于是两个羽人相互搀扶,扑腾着三只羽翼狼狈地飞向夜空,混迹在满天飞翔的羽人之中。
苏安玄回过头来,看见老人正扶着墙慢慢站起来:「您没事吧?」
「还好,多谢相救。我替我们家大小姐谢过少侠。」老人弯下腰来作了个揖。
苏安玄连忙还礼。老人直起身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苏安玄,正想尽说些什么,突然指着苏安玄的右手大吃一惊:「少侠!你……你的手!」
苏安玄一惊,猛然想起右手拇指上的天驱扳指,不禁把手向后一缩。老人家见状,忙上前一步,说:「少侠,不要说没关系,再迟了,你的手可就废了。」
苏安玄甚是疑惑:「这老头子在说什么呀?」但尽管心中疑惑,仍是将手抽出来。这一看,可吓坏了苏安玄。哪里还能看见扳指呀!原来整只右手变得肥大臃肿,连扳指都深深陷入皮肉,几乎看不见了。右手肤色变得殷红,像是充满鲜血的水泡,表面布满黑气。
原来这些并非普通的月季花,而是由花农按特有的配方栽培而成的。配方中加入了鹤顶红、夹竹桃、红茴香等剧毒物。将配方敷在月季花的根系处,久而久之,各种毒素就融入了月季花中,而月季花开花时却会显得更加艳红,极具观赏性。但由于毒素侵蚀的原因,花期短暂,一旦花谢,就会残败不堪,却更有一种凄美之景,故人称其“残月季”。因为品种稀缺和配方造价昂贵,所以只有大户人家里才有观赏。
除此之外,更有中州的诸侯国不惜花重金培植残月季,并纳入军库,借助它的剧毒来攻城拔寨。
就算像苏安玄右手只有一条淡淡的血痕,毒性就会立即发作,而中毒的人却丝毫不会发觉。最终,中毒者会因全身肿胀而亡。
看见苏安玄肿胀的右手,老人严肃地说:「快!用冰敷!只有冰才能压住残月季的火气!」
「可是,现在没有冰呀!」猛然间,苏安玄想起丁掌柜给他的那壶冰蝉。苏安玄马上贴身翻出那壶青瓷瓶,连打开盖子都省了,直接将瓶子摔碎在地上。从青瓷瓶里滚出三颗黑色的小球,拾起来仔细一瞧,才发现原来是三只黑色的蝉蜷缩成球状,每只蝉的背后都有一条沿脊背而下的白线。
苏安玄按照丁掌柜的吩咐,将冰蝉贴着臃肿的右手,双指轻轻一夹,冰蝉沿着背后的白线裂开,喷出一股白雾,黑色的蝉体则渐渐变成白色,像雪一样渐渐溶化,伏在整只手上。苏安玄照样将剩下的两只冰蝉夹碎,白色的浆液裹上了臃肿的右手。苏安玄又撕下一张衣布,紧紧地包着右手,防止冰蝉的寒气散去。
老人静静的站在一旁看着苏安玄处理右手,直到最后才开口:「如果用冰蝉的话,可能要裹上一段时间。今晚你就不要动它吧!”」苏安玄点了点头应答。
这时,门外楼梯上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一抺紫色从门外飘了进来。女子一袭紫色长裙,显得端庄典雅。老人看见到来,马上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
女子望向苏安玄,两人都不禁一愣,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又翻上心头。看着她的眼睛,苏安玄终于明白,在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深处看到的那种难以言状的颜色,正是那端庄典雅而又神秘的紫色。
过了好一会儿,女子才回过头来问老人:「这里发生了什么?」
「回大小姐,有两个羽人想来偷残月季,多亏少侠出手相助,否则残月季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大小姐再次看向苏安玄,后者微微一笑,说:「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在宁州深处的密林里,一个羽人搀扶着另一个受伤的羽人,飞落在一处亭院内。在他们面前,一个高大的人影在若隐若现。一把沙哑的声音穿透黑暗问道:「花呢?」
「原本到手了,结果突然杀出一个人,把花截住了。我们怕还有伏兵,于是不敢再上。」
那把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忧愁:「要是真的像情报中所说的那样,辰月真的拿残月季培植军用,那宁州就不得安宁了。」
「大哥不用担心,下次我们直接将它销毁。」
「只怕有了这次,他们会有所警惕,下次等机会就难了。不过现在也只能等了。还有,那个半路杀出来的人还认得吗?通知各处的兄弟,提防他,遇见他就把他拿下。他很可能就是辰月新的『刀』,对我们很有威胁。」
「是!」两名羽人退下。
黑暗中,不易觉察地传来一声轻叹,消失在鸟鸣山涧之中。
清晨,空气中弥漫着雾气,朦朦胧胧地,像是快要下雨了。鸟儿看不清对方,站在高高的枝头呼叫着。
大小姐走到苏安玄桌前坐下,像是对待多年熟悉的人:「你的手,没事了吧。」
「嗯,都裹了一个晚上了,也该消肿了。应该可以把布卸下来了。」边说着,苏安玄边将包在手上的衣布拆开,「对了,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我从天启来,我姓古,叫古……古思琳……」古思琳的声音渐渐弱小,但苏安玄并没有发觉,他正专心地解开衣布。他的手已经恢复原样了,而那枚天驱扳指正稳稳地扣在右手大拇指上。
后记
那些前世注定的人,是不会错过的。尽管天大地大,总会在安排好的道路上相遇。世界,在真爱面前变得渺小。
这篇《残月季》应该是高二的时候写的,当时杂志社把我遗忘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过。这虽然说是第二部,但其实是第一部的前传。
上一次在公众号重新发第一部的时候,有看过九州的朋友来提意见。为此,我还特地去翻看了九州的编年史,重新确认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对这篇《残月季》进行了一点点改动。如果说第一部只是将一个武侠故事嫁接进九州,那么这一部就完全是一个九州的故事了。九州的历史、九州的地理、九州的种族、九州的民俗、九州的战争还有九州的政治。这是在九州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我在文中穿插提及了很多当时的背景,比如白发鬼(见《葵花白发抄》江南)。之前有朋友说,辰月和天驱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恐怕这位朋友并没有真正了解九州的世界观,辰月和天驱分别继承了墟和荒两个神的意志,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九州世界里最大的分歧。虽说在胤朝末年,以姬野为首的新天驱并没有真正继承荒神的旨意,但他们依旧是一支推翻了被辰月统治的胤朝的强大势力。我还是想重申一次,九州并不是江南一个人的,《缥缈录》也不是九州的全部。
最近听说江南的《缥缈录》再版之后,又有了拍电影的打算。对于九州的兴衰,我想说,成也江南,败也江南。江南终究是个生意佬,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会产生最大价值。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因为九州而得益的,比如知乎段子手唐缺,他就是因为九州而出道奇幻小说的,并且在九州效忠了不短时间,九州作品数量当位前列;还有唐七公子,她的《华胥引》就是九州小说,去年拍成了电视剧,名噪一时(我稍微看了一下电视剧,发现还原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