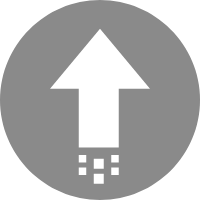正文
其实,我并不信宗教。但要另外说明一点,我是相信所谓的神或鬼的存在的。在我看来,这可以用科学来解释:那些被我们称为神或鬼的东西,是不和我们一个维度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能神通广大忽隐忽现。因此我尊重每个宗教的神灵,即使我不会特意去祭拜它们。
要说起这题目的原因,恐怕就要提一提一位作家:保罗·柯艾略。他有一部小说名字就叫《朝圣》。保罗的另一篇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它被称作《朝圣》的象征性作品。《朝圣》里讲述了保罗在拉姆教派的帮助下,在朝圣的路途中重获新生,找回心之所向的故事。朝圣应该是向敬重的东西表达仰慕的举动吧?但是在这漫长特殊的路途中,恐怕人们会收获更多的东西,比如梦想,比如爱。
我不信教,但依然存在值得我去崇拜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大自然。说出来可能会招来讪笑,“这真是个奇怪的爱好”。我们每天所见所触,难道不是大自然吗?但是我不认同这样的大自然:天空中是个大量的硫化物、氮化物和颗粒物,地上是看不见泥土的混凝土和沥青。于是,我想出去,走出钢铁森林,去看看真正壮美的大自然。我把这个路途看作朝圣并不为过,我们本源于大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大自然本是我们的祖先,去瞻仰他们,难道称不上朝圣吗?
我已记不清何时,又因何事,开始有这种念头,但心里一直有这种冲动,提醒我,要去看看。

第一次有明确的感觉是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一次,我们租了台中巴,跑去了满洲里,然后穿过草原去到大兴安岭,差一点就能去到漠河。车子穿行在草原里的公路上。虽然沿路的电线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但越过茫茫野草,和天际线对视的那一刻,我呆住了,一股无形的压力向我涌来。以我的学识,我知道草原的那一边,还是草原,无边无尽,如果毫无准备的进去了,没准就出不来了。但我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要顶住那股压力,走进草原深处。草原令我担忧,同时也令我兴奋。

第二次就更加明显了,那是在新疆。我们驱车从喀什出发,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戈壁,又从戈壁变成丘陵,最后我竟发现自己处于群山之中。我们在喀拉库里湖下车。一抬头,看见四周全是雪山,像头戴白色尖帽的巨神,将我团团围住。不同于草原上的压力,巨神的目光犹如千斤重,只直压到我头上,似乎要我下跪。耳边寒风呼啸。那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词:“臣服”。我拼命仰着头,凝视雪峰,而它就在那,一动不动。我几乎没有力气举起相机,记录下它们的雄壮,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它们是不可能被束缚在相框里的。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严和神圣。那一次,我被它震撼住了。
而这一次,在西藏,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我直面了大自然,并迫不得已地发起了挑战。对大自然挑战就是场赌博。现在回想起来,我赌上的,弄不好,是我的命。
在米堆冰川,因为旅游开发不完善,没有明确的路牌,我们走错了路。原本沿着山谷底的马道走,很快就能到观景台,但我们却从山谷的侧面爬上了半山腰,并且一直往冰川走,远远地超过了观景台。到后面,甚至都没有路了。可能是冰川构造造成的,从半山腰一直到谷底是堆成一层层阶梯状的乱石堆,大概有六七层。同行的有一位贵州的地理老师,姓王,他想到冰川那看看,于是我们两个就打算从半山腰翻过一层层的石堆下去,顺便找找有没有别的路出去。
王老师本就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对高原气候比较适应,而且他走山路特别快,因此我们之间很快就拉开了一段不短的距离。当我爬到离谷底还有两三层石堆的时候,王老师已经在我的下一层了。我看着时间,预计着:如果我继续爬下去,又如果没找到路,那么再爬上来原路返回可能就不够时间了。于是我打算立即返回。但在此之前,我还得跟王老师打个招呼。由于石层遮挡的原因,我只有拼命爬上一块大石头上才能看见王老师。我向他挥手,四周太空旷,即使只隔了百来米,说话也几乎听不见了。我打了个手势,告诉他我先回去。在确认他明白我说的后,我转身准备爬回去。
一转身,我才发现这将是多么艰辛的路。由于我们之前是斜斜地往下走,并不觉得辛苦,而且下得很快。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原来走了这么远。我看到横向的石头起伏不大,于是打算先垂直爬到我们出来的那个林区,再横向出去,这样应该能快一点。我花了十来分钟爬到半山腰,乱石堆和林区的分界处。我记得来的时候是沿着一条溪流上山的,就打算进入林区,找到那条溪流,沿溪返回。用手机定好方向后,找到一处灌木稀疏的缺口钻了进去。山林里很静,甚至没有鸟叫,只有树叶摩擦的声音。我深入了十来米,却发现前面是一个很高的陡坡。仔细听听,似乎并没有流水声,看来小溪应该是绕到陡坡的后面了。虽然翻过陡坡应该就能找到那条小溪,但在山林里找路无疑是找死,我只好退回山林边缘的乱石堆了。
看来只有沿着边缘才能走出去了。我望了望看不到头的乱石堆,摘下头上的魔术巾,绑在手上防止划伤。那一刻,心里却泛起一阵兴奋。身边是小至沙粒大小,大至两个冰箱大小的石头,下面是相当于二十多层楼的谷底,但我丝毫没有害怕,有的只是兴奋和对时间的担忧。冰川空旷,除了脚下石头松动的声音、呼吸声和心跳声,万籁俱寂,偶尔隐约听到身后的冰川传来隆隆声。与大自然相比,我是多么渺小。我随时可能摔进谷底或者在上山迷路,大自然一动不动就能将我吞噬。但我很兴奋,因为我有机会挑战它,如果赢了,我就能逃出这里。大自然用危险压迫我,我却能奋起抵抗。最后我当然是毫发无损地出来了,但出来后我才发现我的嘴角已经起了泡沫星子。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挑战敬重的东西?对敬重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膜拜么?这和索隆一样,他敬重鹰眼,但同时也在为打败鹰眼而努力。《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水晶店老板将去麦加朝圣看作是生活的支柱,一旦完成了朝圣,他的时候将失去意义。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朝拜敬重的东西不单单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如果那东西真的值得你去敬重,那么它不会在意那无中生有的敬意。在朝圣之路上明白了什么或者变强了,才真正对得起敬重的东西
后记
这篇后记和正文内容毫无关系。
由于一个意外,这篇文章的原稿丢失了,读者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其实是重新再写出来的。在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当年钱钟书为什么在丢失了《百合心》手稿后没有重新再写一次——即使他曾说过那将是比《围城》更精彩的作品。当我在重写的时候,旧稿不能完全记住,但影子却挥之不去,很难写其他东西,总感觉原来写得好。
即使是现在我写完了,还是觉得原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