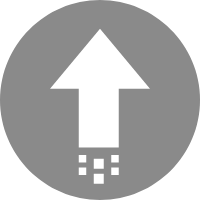写在一开始的后记
这是篇高一时的作品。
说起它的来历也算是机缘巧合。一个要好的初中同学突然碰到我,又恰好我们学校的一个搞杂志的社团纸媒社到的个高干和我同学在一起,又恰好高干正在找连载小说的稿源,又恰好我有一个刚写完大纲的小说。于是单子就接下来了。
然后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章。然后第一章就被登上了那期的《四季》。然后就真的没有然后了。因为社团换届,我就被忽视了。
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套用一句韩寒的话呢?“不想花十几块钱买书的读者可以上网花十几块的电费和上网费把文章全部浏览了。”(我真的不是在打广告,他们资金短缺连稿费都没给我为什么要帮他们打广告!)
这是篇属于“九州”的作品。
身边的人似乎都不知道,或仅仅只是听说过《九州志》。我听说过的人大半是因为江南,他是从《九州志》才开始落草的,啊不,是出小说的。
我是在初二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九州”这个世界。当时同宿舍的从图书馆借回来一本,我顺手就抄起来看。《九州志》的排版到现在都一直没变:一开始是历史,接着才是各路作家的小说。第一次看的时候,对历史不感兴趣,直接看了几篇相对独立的小说。后来才发现这个世界设定的有趣,才开始去看历史。那一本书的历史,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讲的是葵花之世,也就是我的这部小说所处的时代。那是胤朝开国200年后的一段黑暗时期。一羽人古伦俄而为首的辰月控制了整个朝廷,而另一边,天罗草堂的刺客在试图破坏这种控制。帝都天启城内腥风血雨。
当然,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震撼,毕竟这只不过是皇城内的乱斗,一个有能力的作家都能写出来。但当我将历史往前翻,看到蔷薇之世,以及后来的风炎之世、北辰之世,那大国间的壮阔历史让我震惊。特别是风炎之世,风炎皇帝白清羽亲自挥师北征蛮族,蛮族的铁浮屠和华族的重甲山阵在辰月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升级。随着装备升级战事也随之升级,在各种战役和阴谋下,蛮、华两族两败俱伤。期间的描写,堪比真实历史。
于是,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写一部“九州”的小说。我没能力操控《澜州战争》那样的大场面,也就只能写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现在放出来的第一章就是两年前写的第一章,一字没改。一来是为体现我的写作风格,大伙一点一点往后看,或许能看出我在这方面变化;二来是因为懒。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这篇小说在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少东西,甚至在后来高二分班后,还有人因为这篇东西而认出我。朋友们看过的文章如此之多,却又有几位作者能因为这些文章而被记住?作为一个被人记住的写手,这是我的荣幸。我的语文老师Lulu曾在我的一篇随笔后写下这样一句评语:“总有你预想不到的人在注视着你。”
感谢那些默默注视着我的人。
那么,故事开始了。
第一节
官道上,几骑快马被鞭子抽得发狂,没命似地朝前狂奔。在他们身后,大片大片的乌云铺天盖地地涌来,一场暴雨是免不了的了。他们似乎只是想着找间客栈避雨,所以策马狂奔。
很快,前面就出现了一座小镇。因为看见乌云的预兆,镇上的人们都忙着收拾店铺。卖衣服的快手快脚地将衣服叠起来;卖饰品的将饰品尽数收入袋中;推车子喊卖茶叶蛋的老头也将车子推进巷子,用麻布盖上,手上拿着两只刚煮好的茶叶蛋蹲在屋檐下剥壳儿。几家大老字号的伙计在慢吞吞地收拾货品,他们三堆两堆地聚在门口,坐在板凳上聊天。这只是一场偶然打破他们日常的一场暴雨,但经生活长期麻木的他们却并没有过多的反应,他们只觉得这也属于自己的日常的一部分,甚至还为失去赚钱的时间而抱怨。谁也没对几骑快马在意,在他们眼里,那只不过是几个避雨的旅客,几个只为寻找路途上的客栈的旅客。
而月牙客栈则是这座宁州小镇唯一的客栈。客栈的主人是个羽人,却是个凝不出羽翼的羽人。这位在羽人一族的地位近乎奴隶的羽人,在这座城镇中却并不是卑微,有很大成度上是因为他过人的经商能力。月牙客栈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几骑快马,一行七人,全是一身黑衣,黑色的连衣帽压得低低的,很难看清他们的面容。马蹄步步急促结实的点击地面,朝着月牙客栈急奔而去。不多时便停在马棚中,一行人翻身下马,将马拴在马棚里。为首的抬头望了望背后即将逼近的乌云,眼波里静静地泻出一丝杀气,把袖子一挥,带着身后六人走向客栈大门。
大门上插着六只牦牛角,呈月牙型,上面雕满细致的花纹。牦牛角尖向下,整个大门就像一张怪物的大嘴。马儿低喘着气,目送七人的背影,它们只求鲜嫩的牧草,只是进入大嘴的人,还会回来喂它们牧草吗?
天边闪过一道没有雷声的闪电,雨噼里啪啦的开始下起来。乌云越积越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竟如深夜般黑暗,一片朦胧的雨幕笼罩在小镇之上。一阵狂风挂过,雨势猛然加大,雨点沉重地打击地面,奏出一段杂乱的序曲。
骑马者们走进客栈,一个伙记马上迎过来。在这么糟糕的天气下来了生意,换做别人也一定会热情满怀的。只是伙记迎到的却是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这……”伙记迟疑着打开袋子,只见金光四射,袋子里装了满满一袋子金珠。伙记马上会意了,道了声谢谢后便跃过众人,将客栈的大门关上,然后径直上了客栈二楼。
给客栈满满一袋金铢,这一行人并不是路过避雨的旅客,而是专程来找人的。他们要找的人,或是因为仇恨,或是因人所托,总之他们要找那个人打一场。给客栈的一袋金铢,是给他们的战场的赔偿。这是道上的规矩。客栈的伙记拿到钱便会自觉退开,顺带把剩下的食客打发走。
可这时,客栈中只有一位食客。那人大约二十来岁,一身游侠打扮,桌边倚着一把长剑。长剑没有剑鞘,剑身只是用细麻布包着,却没有透出一丝寒光。游侠衣着看出早是经历风沙,一身粗布衣衫风尘仆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刚进来的一行人,只是盯着桌上精致的饭菜,右手拾筷慢慢品尝,左手则摇晃着一只酒杯。在右手的拇指上扣着一只古老的沉青色板指。
桌上除了饭菜,还点着一支蜡烛。原本是大白天,但暴风雨的到来使这里一如黑夜,蜡烛仿佛无尽黑夜的指路灯,只是不知路向何方。
客栈外面早已是暴雨倾盆。雨水顺着插在屋檐的牦牛角滴下来。这六只牦牛角来自瀚州的一只巨型六角牦牛,经过河洛们的精雕细刻,作成精美的月牙形,插在客栈的屋檐上。月牙客栈因此得名。
骑马者们依然没有任何交流,径直走向不同的桌子坐,正好将游侠围坐在中心,除了一个看似为首的仍站在那。待众人都坐定了,那人才踱着步子,走到游侠对面坐下,不知从那拿出一双筷子,也不管对面的人,自顾自地挑起一块鱼肉,放入口中,眯起双眼,似乎十分享受。最后喉头一抬,将鱼肉咽下,啧啧道:“唔,天拓海鲈,用冰蝉冰鲜着从瀚州运过来,待冰融化立即上桌,还配上醉青阳酒,口感果真脆嫩。店主人不亏是与瀚州长期交往的人,在宁州如此美味实属罕见。”
这声音并不怎么好听,又沙又沉,倒是衬上了他一身黑衣和屋外的雷雨声。但那位游侠似乎并不怎么介意,依旧慢品慢尝。桌上烛焰晃动,烛光照在两个人面上。
游侠看起来很年轻,一脸英俊,眉宇间透出三分机警,三分冷静,外加三分稳重,还有一分天真。下巴没有须髯,嘴角却似乎还带着一丝冷笑。
与其相反,骑马者的头目则大有不同。他面容粗暴,正与那把又沙又沉的嗓音一样,坑洼不平,右面颊上留有一条刀印,双目中透出血腥。一身黑衣上浮着一条条错杂的纹路,像一条条噬血的毒蛇。在烛光下,宛如毒蛇吐信。
“前辈假如喜欢,可以叫店家再做一盘,为何还要支走小二,与晚生共食一盘?前辈若喜欢,晚生做庄,这餐是晚生请前辈的。”游侠开口了。
“对吃的东西,老夫只不过是略知一二,说出来贻笑大方还可以。况且老夫喜欢的,并不是金钱所能换来的,而是要自己争取的。”
“哦,请前辈一叙。”
黑衣人嘴角一钩:“杀戳。”屋外十分适时的闪过一道电光,一声雷就在小镇上空炸响。雷声过后,屋内一片寂静,只有屋顶上传来的暴雨声,杂乱地、无序地,在空寂中荡开。
“辰月的人只懂得杀戳吗?”游侠的话中没有带起任何情感,只是放下酒杯筷子,十指交叉,下意识地摸了下拇指上的扳指。
“不错,我们为了权力而杀戳,为了权力我们会不惜代价。这是神的旨意,任何挡在我们面前的人都要杀。我们为神谕不带任何情感!”沙沉的嗓音在无序的雨声中显得更加深沉。
黑衣人在最后两个字稍微加重了声音,游侠抚在板指上的手指不禁一顿。黑衣人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不再继续说话,拿起桌上的酒壶自斟自饮起来。
外面的风雨逾加猛烈,就像殇州雪山深处的巨兽在咆哮,风把大块大块的雨水往窗上门上砸去,窗纸啪啪作响,却愣是不透进一丝寒风、一滴碎雨。整座客栈就像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密闭空间,无论外面多么狂风暴雨,在客栈里,时间似乎凝固着,没有声音,就连气息也似乎是胶着着。整个气氛,就如夏日暴风雨前夜的寂静,闷热,令人窒息。
狩猎者要学会等待,等待猎物的松懈,然后致命一击。
猎物也要学会等待,等待猎人的疏忽,伺机逃生。
可是又有谁知道,猎物会不会反咬一口。谁是猎人,谁是猎物,只有在最后一刻才会清楚。不管是智警狠辣的猎人,还是饿极凶残的猎物,结果都是不可预见的。
第二节
在宁州与中州交界的一座小城,这里没有风雨,云淡风清,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被重兵把守。在屋子周围有规律地游荡着几个黑衣人,他们沉默不语,深邃的目光如同黑洞,吸引着无数路人的偷瞥。
几乎整个城市的人都在讨论着这间一夜之间被改变命运的屋子和屋子里的人。里面的人是羽族的某个贵族?还是中州皇帝老儿派来的使者?这都无人知晓。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很有派头的人。他的手下不阻止人们去讨论,去猜测他,这就足够了。因为他们只需要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二楼的窗架被轻轻放下,男人的目光从无知的路人上收回,重新投向屋内,投入那个戴着面具的人。后者正在泡一壶铁松针茶,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松树,其色如铁,茶色亦如铁般沉厚。
男人在狰狞的面具前坐下:“做得这么招摇,你就不怕宁州的逆党突然来袭?”
“这座城市已经被封锁了,就连商队都没法进入。消息只能在城市内传播,让那些无知的草民欢愉一早上,有什么不好?”
“真正能让他们欢愉的,只有钱。”男举起茶杯,“怎么,只请我喝茶?我看对面那家客栈的酒不错,有点劲头。”
“酒会让人不清醒。”
“就像当年的你。”男人嘻笑道。
突然,狰狞的面具里的那双眼睛闪过一丝杀气,如残狼,毒狠而又迅速,却在一眨眼就消失贻尽,仿佛那一切都不曾存在。
男人心里就像炸了一声惊雷,他镇定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额,那……你派出的人能解决吗?”
“不,那只是几枚弃子,用来钩起他的回忆,使他像酒一样不清醒。”声音里没有任何情感,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剩下冷静。
“他们都是棋子,受人操纵,受人任用,没有惜怜。”
“你又错了。芸芸众生都是棋子,不单是他们,也包括你我。天下就是一个棋盘,每个人都被操纵着,跨向必定要走的那一步。下子的不是教宗,更不是皇帝老儿,没有人配,也没有人拥有这个权力,除了神。只有神才拥有下子的权力,而我们,正是奉神谕行事。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这样换子值吗?”
“用几只‘卒’换一只‘车’,你说值吗?”
“很难说,况且换取的并没有整只‘车’,能否在‘车’上留下阴影还很难说。这世上风云变化,谁又知道自己算漏了什么,或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意外。”
“那就看神的旨意吧。”
男人低头看向手中的茶,其色如铁,沉重的压在手心。
在宁州的另一边,风雨依旧,窒息的气氛依旧。
客栈外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丝毫没有惊动屋内的人,他们默默地坐在那。有的在轻抚手中的剑,一遍又一遍;有的整理衣上的褶皱,一遍又一遍;有的无声地指击桌面,一遍又一遍。他们不相互张望,仿佛互不相识。
其实他们确实并不相识,只是任务将他们编织在一起。他们只知道要在一起,按照计划杀掉眼前这个人,然后就可以各自归去。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接到任务就去完成,无须任何解释。他们只须明白,自己在按神谕办事,这就满足了。
为首的黑衣人仍在喝酒,桌上已经摆上三尊空的青瓷酒瓶,但黑衣人脸上丝毫没有泛起半片红晕。第四尊青瓷酒瓶在他手里,一滴滴将酒送入他口中。最后,像挤尽生命般,滴下最后一滴酒。黑衣人咂了咂嘴,将酒瓶轻轻往桌面一放。
酒瓶乍破,声如裂帛,干脆而又清亮,瓷片并没像水波一样像四面荡开,而是只朝着一个方向游射出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那张英俊的脸。
游侠从碗里夹起一块鱼肉,向空中抛起,鱼肉沿弧线运动,一下子撞开了几块瓷片。鱼肉虽软,却在与瓷片撞击的瞬间发出铁器相击的声音。随后,游侠食中两指夹着一双筷子飞快地旋转起来,拨开其余的瓷片。瓷片纷纷落地,如冰块落地一般,在地上碎成粉碎。
就在这一瞬息之间,隔桌的黑衣人已经离开座位,向后退去,游侠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发起进攻,但有一点很明确,战斗已经开始了,已经不可避免了,接下来就是狡诈的猎人和饿极的狼的厮杀,胜者生,负者亡。
屋外依然狂风暴雨,狂风暴雨依然吹不进这栋铁笼似的屋子。但是屋子里却开始起风了。烛光开始摇曳,有序地,却是一次比一次幅度大。纵使是明眼人也能看到,酒杯上残留的酒面上,蒙上一层淡白色的霜。气温在下降,伴随着渐渐加大的风力,寒意入骨。
蜡烛上的火焰忽明忽暗,最终,在一声惊雷之中猛烈地一震,烛光熄灭。整栋屋子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任何声音在这时候只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只要没有闪电,现在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而在明处的人,将会很快被对方抹杀。
但是战斗总要有个输赢,熄来蜡烛的计划并不是只求自身安全,因为他们才是狩猎者。黑暗出现四点光亮,像刚被重新点燃的蜡烛,只是悬在空中,并且渐渐变大,最终形成四个火球。
四个火球一齐围上游侠,光亮立即使游侠暴露无疑。更奇特的是,四个火球都只向着游侠一面发光,向其余面则像罩上了灯罩。这意味着黑衣人们仍在暗处。
『郁非秘术』。
『印池秘术』。
四个火球是由黑衣人中的郁非秘术师发出来的,而刺骨严寒则是由印池秘术师发出来的。黑衣人中至少有两个秘术师。游侠不禁暗暗叫苦:不要再有更多了!
四个火球围着游侠开始旋转发亮,可在寒冷中,游侠丝毫不感到暖意。他站在光亮中,没有任何动作。再多的动作也会被敌人看在眼里,自己却不知敌人有何动作,他能做到的就是站在那里,细细聆听。
也仅是一眨眼的功失,游侠擞地一扬眉,右手挥出,两只筷子向不同的地方疾矢而去。在明处的人必须尽快脱离光明,必须主动抢在暗处的人之前出手,否则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听见风声,两位秘术师都不禁吓了一跳。两只筷子的去向竟是自己。
郁非秘术师离得较近,完全没有反应的机会,筷子洞穿他的胸膛,带着一丝血腥,扎在后面的墙壁上。他的瞳孔顿然收缩,惊惶和不解,在黑暗中的脸上展现,却没有人看得见。恐惧加快血液向心脏回流,却从伤口处激射而出。最后惊惶和不解在脸上凝固,成为没有人看见的战争的艺术品。
接下来就轮到印池秘术师,他还有时间应变,袖中的手指飞快地画动,一栋冰墙瞬间筑起,挡在他面前。他微微轻松一口气,却听见黑暗中“吱啦”一声,筷子竟然穿破冰墙,带着嗖嗖寒意,直扎胸膛,只是力道已经被削弱,无法洞穿,却已经扎进三分之二,而位置也正是心脏。印池秘术师双眼一翻,当场弊命。
他们两个到死也不知道,是他们结印时,手指在衣袖中画出的风声出卖了他们的位置,成为这场战斗首先阵亡的人。
第三节
四个火球和严寒随着秘术师的死亡而泯灭,化为一片星火散落下去。有一片星火散落在蜡烛上,竟把蜡烛重新点燃,顿时,屋内恢复光明。这一瞬游侠看清了黑衣人们的位置,一共还有五个,呈五角星形排布,为首的站在东南面上,他们手上都已执着出鞘的兵器。
下一瞬,五个人同时兵刃出鞘,直击游侠。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打乱了,只有硬碰硬才有活下去的道路。
游侠拿起被细麻布包着的长剑,迎上了北面的敌人。那是个瘦子,手执一把又细又长的剑刃。两把兵器相碰,游侠手腕一抖,细麻布一下子被炸破,露出剑身。瘦子则被内力震伤,虎口破裂,兵刃脱手飞出,身形向后跌去,昏迷不醒。游侠顺势在对方的兵刃上弹出一指,兵刃改变了飞行方向,朝着东面的人扎去。东面的敌人始料不及,完全没有反应,就死在了队友的剑下。
西面和西南面的黑衣人见状,挻剑从两个方向攻入。游侠一脚踢起桌子,阻住来剑,而桌上的饭菜酒壶则砸向他们。两人被淋得一身酒肉,狼狈不堪,剑又扎在桌上,正欲奋力拔剑,只见白光一闪,双手毫无知觉地断开,接着喉头一甜,一股内力从后背击入,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最后双眼昏麻,跌在地上,他们并不知道,身后被击上一个猩红的大掌印,掌毒攻心,带着无知走上了黄泉路。
现在仍然站着的就只剩下他们的头目,他目睹着游侠在几个起落间击倒了四名手下,开始慌张起来。他的确低估了眼前的对手,纵使他依然是个狩猎者。他从教长那接到任务后,还嫌两个秘术师太过多余,现在他开始后悔了。这是他见过最强的人,但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敌人。难怪他们的名字让教长甚至教宗头痛不已。
他不禁抓紧了拳头。教长的任务不能空手而归,要不提着敌人的头颅回去,要不就提着自己的头颅回去。
地上躺着六个人,只有一个还活着,但已经身负重伤。游侠站在原地,右手执剑,眼中射出凌利的目光。古铜色的剑身上布满古老的纹络,在破布而出时,并没有散出骇人的寒气,有的却是历史的沧桑。没有沾上血痕的剑仿佛只是一个艺术品,游侠握着它,更显稳重,一股无形的气场震慑着对面的敌人。
望着游侠的眼睛,黑衣人感到一种被俯视的感觉,压力如山般压在他心头。黑衣人汗如雨下,猛然暴啸一声,飞身而起,双眼如毒蛇吐信般猩红,右面颊的刀印更加狰狞。他一扬袖子,抓着两把短剑击向游侠面门。游侠挥剑阻挡,没有清脆的兵刃相击的声音,却传来一声沉铁撞击的闷响。一把短剑滑开,跌落在地上,黑衣人的另一把短剑也荡开,门路大开。游侠圈转剑身向黑衣人心口刺去。
黑衣人向后急撤,但剑锋依然跟上他胸口。眼见剑锋刺上,黑衣人突然用那把又沙又重的嗓子奋力喊道:“教长已经给琳儿发下任务了,目标就是……”就如一声惊雷乍响,原本平稳准急的剑锋突然猛烈地抖动了一下。他的心被狠狠地刺伤,不是利器,也不是任何有形之物,却是黑衣人的话。这句话竟使他差点松开了剑。但是剑还是送入了胸口,黑衣人留下半句话,带着剑倒了下去。
游侠无力似的松开了剑任由敌人带着它倒下。他从未试过在战场上松开剑,即使在敌人被击毙使,因为在战场上紧握手中剑的人,才能紧握自己的未来。但这次他却松开了,像当年不由自主地松开那只手一样。
他的眼睛里的凌利荡然无存,有的只剩茫然,脑海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那半句话,窒息笼罩着他。他不想想那件事,可他却仍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件事。
他征征地望着闪动的烛光,丝毫没有发觉地上有一只手慢慢握紧了短剑。下一刻,黑色身形飞起,一道寒光划向游侠。他居然没有一点反应,等到寒气临近,他才恍然醒悟,抬手阻格,才发现手中的剑早已松开。刚才那一剑确实刺进了胸口,但因为游侠的震惊,剑尖被抖开了,并没有刺中要害。
黑色身形带着胸口上的古剑直扑而来,眼睛中似乎带着狂野和讥笑。就在黑衣人手上的短剑向游侠颈处砍去时,仿佛飞梭的石头撞入了浓稠的蜂蜜,黑衣人整个身形开始缓滞下来,最终短剑停滞在空中,颤抖着,想尽力挥下却无力使出。他脸颊上的伤疤在抽搐着,满眼不甘,身体晃了晃便倒在地上。在他身后,一支羽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
客栈外,小镇溶在雨水中,闪电如银蛇般窜出乌云,雷声仿佛死神的脚步。街巷上没有一个人,宛如一座空城,死气笼罩着它,任由雨水猛烈的冲刷。街边的积水中,错杂的水波不断碰撞、消融、重生,水中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
客栈角处的楼梯上,羽人缓缓放下弓箭,走下楼梯,游侠看着地上的人,思绪乱极了。被羽人的箭射中还能站起来,那么这就一定是个不合格的羽人。地上的人永远也不会再站起来了。
羽人走到游侠跟前,举起右手,拇指上扣着与游侠一样的扳指。“铁甲依然在。”羽人说道。
“铁甲依然在。”游侠无心地回应道,心思却完全不在这。
羽人转向地上插着箭羽的人,蹲下下身来,在他的黑衣内翻找着,不多时掏出一只锦囊。锦囊内竟是一只胀着鼓膜的蟾蜍。
“原来是相思蟾,难怪他们能跟过来。苏安玄,你……唉……”羽人欲言又止。
“我知道。我努力去忘记她,可是当我以为心里没有她时,才发现其实她又躲进更深的地方。丁掌柜,你是看着我过来的,我该怎么办?”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这恐怕也只能靠你自己了。”羽人轻拨弓弦,将剩下一个敌人射杀“对付他们不能手下留情,自古以来我们和他们势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羽人看了看苏安玄,后者眼光迷乱。羽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想说什么,但又止住了,转身走上二楼。
留下苏安玄一个站在原地,七具尸体在闪电中用早已灰沉的眼睛望着他。屋外雷声轰鸣,大雨无止的倾泻下来,整个小镇在雨水中朦胧不清。屋檐上月牙形的牦牛角仍在滴水,水滴滴在下面的石板上,溅起水花,发出清脆的响声。滴水声在暴雨声中微弱地回荡,悠长哀婉,如杜鹃啼血,扬出丝丝哀愁。
一滴、一滴、又一滴……
再往宁州深入,暴雨一直沿伸到这里。宁州深处的大森林里,一骑快马急驰着,骑手身上早已湿透,却死死地护着胸前的油布包,不让它被雨水打湿。
飞马溅开积水,惊飞了树脚避雨的鸟儿。在雷声的轰鸣中,快马闯入一处亭院,骑手翻身下马,一边飞奔进竹屋,一边开油布包。油布包里是一封信,骑手恭恭敬敬地将信递上。